孙荪老师的友情,如同久远古惑仔岁月中的醇酒,流淌在演唱会的每一曲,每一次回响,都让人感受到那份珍贵与深厚。他的学识和才气,就像我少年时仰慕的星光,后来因为文学而成为我的老师和挚友。孙老师是永城刘河乡的人,他十八岁便负笈求学,一直到五十多年,他以道德文章誉满天下,是一个著名的文学评论家、散文家、书法家,也是永城人的骄傲。我虽在永城,而他在郑州,但我们之间的情谊却能通过电话和节日问候传递。

2012年,我将出版一本散文集去郑州校对清样时顺便看望孙老师。他兴奋得很,不仅祝贺我,还亲笔题写了书名,为我的作品增添了不少光彩。而2015年,当我的三卷本历史文化散文《文化永城》、《魅力永城》、《风情永城》出版时,孙老师即使患有眼疾,也欣然为之作序。这份提携与关爱,在我们之间更显重要。
当我带着两瓶远方朋友送的酒,以及酂城糟鱼去见他时,他笑容满面,有长者风范,更增加了我对他的钦敬。那句杜甫诗“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,今夕复何夕,共此灯烛光。”就如同描述离别聚首的心境,让我们在短暂相聚中感受时间飞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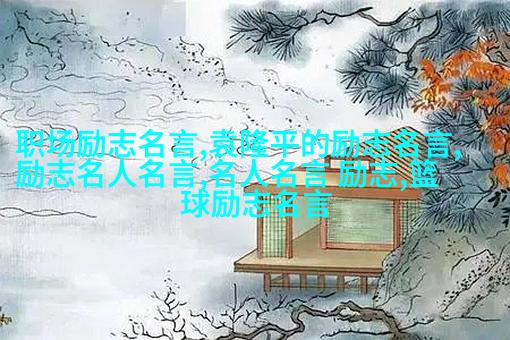
随后,我向他借了一幅书法作品,那是一句唐朝诗人杜荀鹤的话:“就船买得鱼偏美,踏雪沽来酒倍香。”这句话心灵相通,让我明白真正的情谊胜过千言万语。在山静云动、惠风广布间,我们仿佛能听到千里传音,只因有彼此。
鉴于孙老师的地位,他被请写一篇关于永城市历史文化的文章,即使病重也坚持完成。他抱病工作,将《永城赋》写得既丰富又精妙,而他用行草书体所书之匾额,则更加令人赞叹。

最后,当河南省作家协会设立太丘古镇创作基地,我被托付以请他题匾,这个“太丘书院”,也是他应允的一件事情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领悟到,无论身处何种环境,只要心存真诚,便能找到知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