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荪老师年长我十多岁,是文学界的楷模,我少年时便仰慕他的学识与才气,如今已成为我的老师和挚友。尽管我们相隔遥远,但彼此的友情却如美酒一般,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发浓郁。

2012年的春天,我携散文集去郑州校对清样时拜访了孙老师。他异常兴奋,为我的书名题字,还在我即将出版三卷本历史文化散文《文化永城》、《魅力永城》、《风情永城》时作序。我知道他当时还患有眼疾,却仍然不顾身体,写下了那篇脍炙人口的序言。
2015年,当我的书籍杀青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之际,孙老师百忙之中又为我撰写序言。这次,他更是抱病工作,用尽全力,为故乡略尽绵薄之力。在这期间,我们之间除了深厚的情谊,更有提携、关爱、期许相互间传递。

在一次见面中,我带来了远方朋友送来的两瓶好酒,以及酂城糟鱼,这些都是永城特产。孙老师出门相迎,一脸笑容,让人感受到了他的真诚与高尚。他邀请我共进午餐,那一刻,我们仿佛回到了从前,无话不谈的情趣与共鸣,让人感慨万千。
后来,他以赋体形式,为故乡撰写了一篇文章《永城赋》,展现了他对故土深厚的情感和对文化传承的责任。当他用自己擅长的行草书体书写完毕,并赠予故乡,那份赤子情怀跃然纸上,让人敬佩不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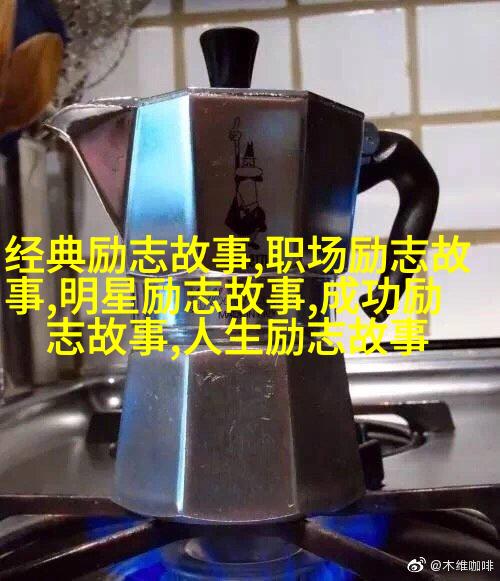
直到红日西坠,我们依依不舍地道别。那一刻,我想起了一首古诗:“山竹绕茅舍,庭中有寒泉。西边双石峰,引望堪忘年。”那句“忘年”让人思索,不知何时能再次重逢。但我们的友情,如同美酒一样,只要心存记忆,它就不会消失。
